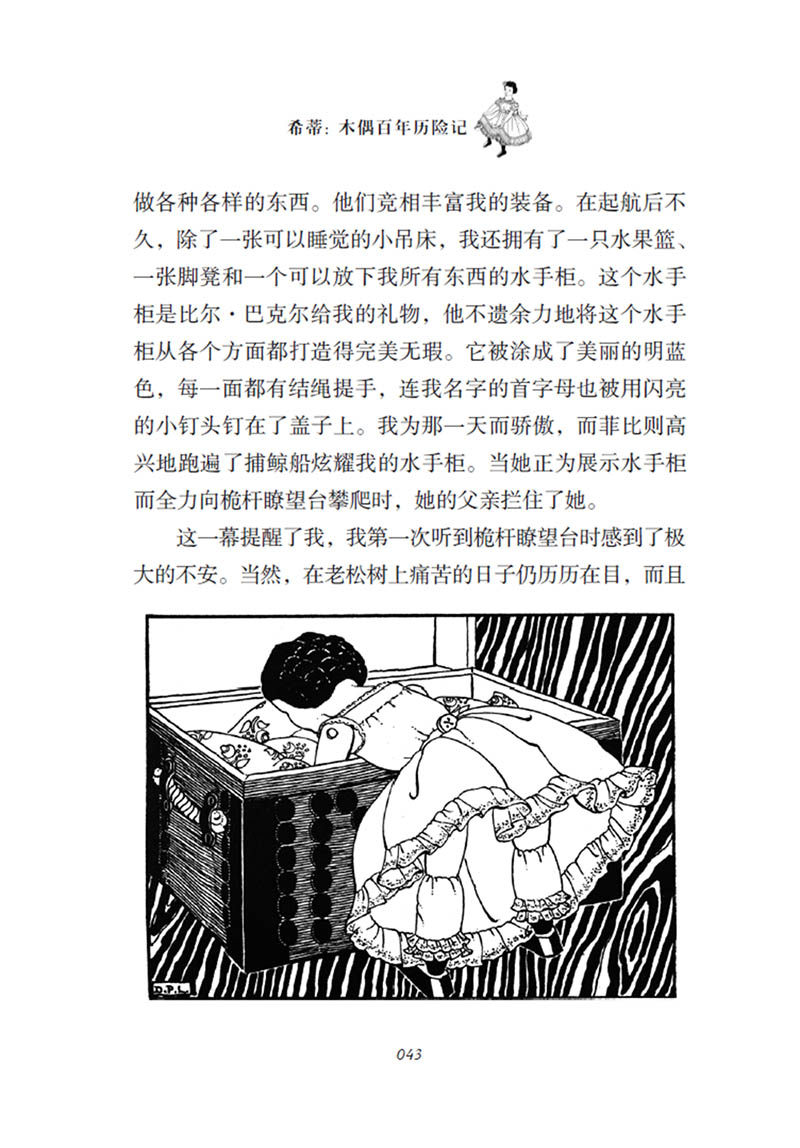一只木偶娃娃曾跟随着水手一起体验过惊险刺激的海上生活,也曾逃脱过水岛土著的魔爪;还当过画家的模特、展览会上的明星……希蒂的这“一生”,既感受到了来自人间的无比温暖和关怀,也体验到了世态的无常和炎凉,但她始终对人间的一切充满憧憬,对她关注的人充满爱与祝福。
《国际大奖儿童小说》丛书从世界各国获奖的儿童文学作品中精选经典,把当今**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推荐给中国的少年儿童。这些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会带给孩子们丰富的阅读体验,犹如一扇扇窗,让他们看到丰富多彩的世界。收入《国际大奖儿童小说》丛书的作品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格调健康,品位出众,能让青少年读者受益终生。有的作品列入学校推荐书目。
《国际大奖儿童小说》丛书涵盖的奖项有:纽伯瑞儿童文学奖、卡内基文学奖、美国图书馆协会奖、刘易斯卡洛尔书架奖、德国青少年文学奖等著名儿童文学奖等。
希蒂的魅力让人无法抗拒。
——美国《国家》杂志
希蒂被描写得栩栩如生,就像一个真实存在过的人,关于她的故事是雷切尔菲尔德写过的最好的作品。
——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
关于第一个夏天,我能写满很多页纸——写普雷布尔船长带我们乘坐双轮轻便马车去波特兰、巴思和附近的农庄旅行;写在旧的南瓜色平底小渔船里他用自制的船帆教安迪航海;写邻居和亲属在如今的好天气里经常前来拜访。在夏季总是很短暂的北方,这样白昼时间长、蔚蓝无垠、阳光明媚的天气是多么美妙啊!所有的花朵似乎都竞相在此刻开放。当金凤花、雏菊和山柳兰还在田地里盛开的时候,野玫瑰已经绽放了自己娇嫩的花瓣,而在最后一片野玫瑰花瓣凋落之前,安妮女王的蕾丝和秋麒麟草已经开始迫不及待地钻出地面。然后就有成篮的浆果可以去采摘。所有的人都说,从未有过这样的季节,尤其适合野生覆盆子的生长。的确,正是由于它们,我才如此快地忘情于世界。
事情是这样的:普雷布尔夫人让我们再去采一些覆盆子以便储存。安迪和菲比打算去不到一英里远的一小片地方,几天前我们刚刚去那儿采摘过。安迪拿着一只大的细藤条篮子,菲比拿着一只小的,而我被放在小藤条篮子里。菲比将车前草的叶子整齐地铺在篮子底上,感觉既凉爽又平坦。那是七月末的一个下午,天气炎热,我很感激能够远离公路的尘土和耀目的阳光。对我来说,这再一次让我感到做一个娃娃真好。唉!但很快我就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当我们来到那小片覆盆子地时,已经有人先我们来过了。灌木丛已经被破坏得“弯下腰来”,而且几乎一颗覆盆子也没留下。
“有一个地方,离海滨不远。”就在他们失望地准备转身离开时,安迪突然想起来了。“走到折返湾后,沿着海滩继续走,一直走到一块林间空地。那里的覆盆子几乎有我两个大拇指放到一起这么大。”“可是妈妈说我们不能远离收费关卡,”菲比提醒安迪,“无论如何不能跑到那儿的视野之外。”“那,”安迪是一个不轻易放弃自己想法的人,“是她让我们来采覆盆子的,不是吗?可这儿已经没有覆盆子了。”这一点无可否认,甚至有点儿说服了菲比忘掉母亲的话。很快我们就向着折返湾出发了,路上我们穿过了一大片茂密的云杉林,密集的云杉树之间只有一条游丝般狭窄的羊肠小道。
“我听到艾布纳·霍克斯昨天晚上告诉你妈妈,附近又有印第安人了。”安迪对菲比说,“他说那是帕萨马科迪人,有许多。他们现在开始卖篮子和其他东西,但是他说不能相信在这附近的帕萨马科迪人。
如果我们碰到他们,最好要当心。”菲比颤抖起来。
“我害怕印第安人。”菲比说。
“来吧,”安迪鼓励道,“我们就要从这儿拐弯去折返湾了。我们将不得不走一段石头路了。”那是一段相当难走的路,石头在烈日下暴晒了几个小时已经变得滚烫。即使穿着拖鞋,菲比依然抱怨着,而赤脚的安迪则边叫边从一块石头跳到另一块石头上。他始终沿着海边走,借飞溅起的水花给双脚降温,所以他们用了好一段时间才到达那片覆盆子地并开始采摘。菲比把我舒服地放在空地边缘一棵有节疤的老云杉树树根之间,在那儿我能看到他们在灌木丛中移动。有时荆棘生长得很高,我只能看到他们的头,就像两个圆苹果,一个黄色的,一个红色的,在绿树丛上方上下晃动。
折返湾畔宁静而美好。云杉树枝低垂入水,树梢则深暗尖峭,犹如上百支箭头直射云霄。海水碧蓝闪烁,白色的扇形小泡沫不断地敲打着遥远的牛岛岸边。空气中充斥着蜜蜂和鸟儿的呜叫和海水冲刷沿岸卵石的声音,以及安迪和菲比采摘时彼此的呼唤声。世界上再没有其他娃娃像我一样觉得如此满足。
突然,没有任何先兆,我听到菲比发出了一声尖叫。
“印第安人!安迪,印第安人!”我看到她指向了我身后的树林。她的眼睛和安迪的眼睛都睁得像门把手一样圆。可是我什么也没看到,因为我的头不能转动。安迪抓住菲比的手,一起向相反的方向跑去。他们沿着海滩飞奔,卵石在他们脚下咯吱作响,覆盆子随着他们的脚步从篮子里不断滚落。很快他们就消失在树林中了,没有回过头来看一眼。起初,我不能相信他们把我忘了。但是毫无疑问,事实就是这样的。独自一人在那儿等待是很可怕的,尤其是听到身后的树枝不断被折断,还有声音咕哝着无法理解的奇怪语言。
她们只是五六个穿着鹿皮鞋、戴着串珠、披着毛毯的北印第安女子,也是为了采摘覆盆子而来的。没有人注意到云杉根部的我。我看着她们将覆盆子装满自己的编织篮,心想,虽然她们的头发是褐色的,而且还有点脏,但她们看上去又胖又和善。她们中的一个后背上还背着个孩子,小孩儿明亮的小眼睛从毯子里望出来,就像旱獭从自己的洞里向外张望一样。差不多日落时分,她们才带着装满覆盆子的篮子穿过树林跋涉而去。
我想:“现在,安迪和菲比就要回来接我了。”但是,随着太阳逐渐西沉,并最终隐匿在树林后面,我开始有点儿担心了。现在天空烧着晚霞,海鸥结伴飞往牛岛。当它们飞翔的时候,我能够在它们的翅膀上看到落日。如果是和菲比和安迪在一起,这样的景色对我来说将会是多么美妙啊。我忽然觉得自己失去了亲人,而且感觉自己很渺小。但是,与我即将要感受到的相比,这几乎就不算什么。
……P1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