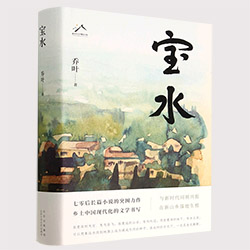
《宝水》是七零后代表作家乔叶的长篇突围之作。太行山深处的宝水村正在由传统型乡村转变为以文旅为特色的新型乡村,生机和活力重新焕发出来。人到中年的地青萍被严重的失眠症所困,提前退休后从象城来到宝水村帮朋友经营民宿。她怀着复杂的情感深度参与村庄的具体事务,以鲜明的主观在场性见证着新时代背景下乡村丰富而深刻的嬗变,自身的沉疴也被逐渐治*愈,终于在宝水村落地生根。 这部长篇是乡土中国现代化的文学书写力作,生动地呈现了中国乡村正在发生的巨变。冬——春,春——夏,夏——秋,秋——冬,四个章节如同一幅长卷,在四时节序中将当下的乡村生活娓娓道来。宝水,这个既虚且实的小小村落,是久违了的文学里的中国乡村。它的神经末梢链接着新时代乡村建设的生动图景,链接着当下中国的典型乡村样态,也链接着无数人心里的城乡结合部。村子里那些平朴的人们,发散和衍生出诸多清新鲜活的故事,大量丰饶微妙的隐秘在其中暗潮涌动,如同涓涓细流终成江河。
老原带的菜有七八样,荤素都有,凉菜装盘,热菜回锅,铺排起来也是一桌像样的小席面。开了一瓶“怀川醉”,他们喝着,我吃着,三个人漫无边际地聊着。这里聊天不叫聊天,叫扯云话。次听到“扯云话”,美妙得让我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天马行空,白云苍狗,无主题闲聊可不就是如云一般?还有“扯”这个动词,扯云,啧啧。 几杯下去,老原说起厨师的事。我说不是先定菜单么?老原说这还分啥先后。就是分先后,也是得先定了厨师。要是先定菜单,厨师不会做咋办?我点头说是这个理儿。两人就笑。孟胡子说,你还真容易被说服。咱这宝水村的民宿有啥了不得的菜,做不了的厨师还能叫厨师?被他俩调侃得,我自觉像个傻子,只好不作声,任他们说去。 原来孟胡子的建议人选是老安。就讲起了安家的事。孟胡子说,老安走到这一步,也是本故事。村里就这一户姓安,既小门小姓,还几代单传,老安这一辈也只有一个儿子。好在儿子争气,书读得好,硕士毕业后留在了武汉工作。老安平日里看着木讷,却也是娇养大的,脾气冲,茬子硬,喜欢要人强,可在这村里势单力薄,发作不起,也只能忍,自觉被挤压着,也不知攒了多少气在肚里。儿子在武汉一成家,他就动了离村的心思。打定了主意,谁劝也不听。虽说村里已经有了要“美丽”的动静,可他既没当真也不在意,三下五除二地就把房子低价转给了张有富。张有富是会计,是多会算账的主儿?他有一儿一女,按规矩只能有老宅这一处,难有新地方。前些年儿子在山下镇上落了户,他们两口子去帮忙看孙子,他十天半月回村来拢一回账目,啥都不耽搁。村里开始“美丽”后,王老板闻风来做民宿,他就眼疾手快地把自家老宅租了出去。租完了又碰上老安卖房子,便立马买下来。说既是现成房子,省得再盖。旧是旧了些,可一拾掇,照样住得妥妥的。又和老宅挨着。将来有个山高水低,把这房子留给闺女,两个孩子挨着住,多亲香。做老人的对儿对女也算是一碗水端平。这几条说出来,条条都是圆满。 我问,大英不也只是一个儿子,为啥有两处宅基?孟胡子道,东掌那处是她大伯哥光明的。光明家没人在这里住啦。光明的事你们听说了吧?当年修叠彩路时遇到了大塌方,他爹是支书,冲在前头,当时就叫砸死了。光明砸成了重伤,还挨了两三年。县里给了笔抚恤金,光明媳妇就带着俩孩儿下山过活,不再回来,这宅基地也不能给外人,自然就成了兄弟家的。我说,听大英讲她和光辉是修路时谈的恋爱,也是那时候?孟胡子说,左右差不多,少说也得有三四十年。四十年整。老原突然说。啥?我和孟胡子异口同声。光明死了四十年整。我和孟胡子一起看着他。他说,我奶奶也是为修那条路死的,就那时候。说完一饮而尽,酒杯咣当一声砸在了桌上。静了片刻,孟胡子说,没听人提起过。老原说,我也不想提。不提了,不提。孟胡子便给老原又斟满,敬过去道,我进村入户调研时就听说了,原家祖辈德行好啊。老原一饮而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