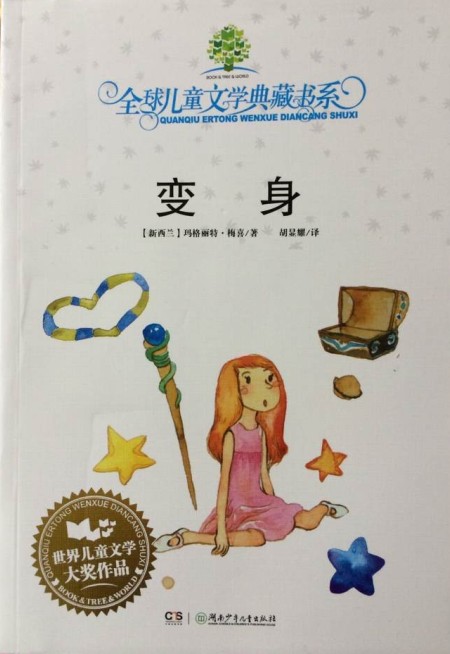
劳拉,一位有着超自然潜力的14岁女孩,在准确预知父母离异、父亲离开等事实后的一天早晨。又收到了“警告”:弟弟杰科被死魂灵布拉克附身。幼小的生命在不断流逝.医生无能为力、母亲凯特伤心绝望。知晓原因的劳拉又该如何呢……故事在一层层悬念中展开。最终,勇敢独立、充满朝气的劳拉历经重重困难,变身为女巫,在索里的帮助下救回了杰科。
惊险的魔幻、温馨的亲情、朦胧的爱情相互冲突与融合,梅喜创造了这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在整个故事的叙述中,劳拉与死魂灵布拉克的对立冲突,劳拉与母亲凯特之间相互依赖、占有却又渴望独立自由的矛盾冲突,劳拉与索里之间的惺惺相惜和朦胧的情感碰撞,变身前的劳拉与变身后更为成熟的劳拉,使小说富有趣味与紧张气氛,充满张力。青春热情的劳拉、年轻神秘的索里、可爱无邪的杰科、邪恶可悲的布拉克、亲切成熟的克里斯、哆嗦善良的范博纳太太……一个个人物形象生动地跃入读者的脑海中,让我们心情随着人物的情绪变化而激荡起伏。“变身”正像我们一段真实的成长过程,一次生命的蜕变。尽管成长的道路困难曲折,充满变化与迷茫,但经过风雨总能见彩虹,我们仍将继续前进。本书在1984年获得英国卡耐基文学奖。
第1章 警告
洗发水瓶子上印着“巴黎牌”,标签上的漂亮女孩在埃菲尔铁塔下露着肩膀。可是下面的一行小字却没法不说实话:新西兰,帕拉帕拉乌姆镇“维斯顿实验室”生产。
有那么一会儿,劳拉忽然有点恍惚,觉得自己好像刚刚洗了头,冲了澡,一下子漂亮得不可思议,正在巴黎街头闲逛呢。不过如果要去的地方仅仅是离惠灵顿40分钟的帕拉帕拉乌姆,这头可就洗得太没劲了。更糟的是,上课前头发肯定干不了,整个上午都得忍受耳朵后面凉飕飕的痛苦。鸡毛蒜皮填满了每天的生活,“新西兰生产”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在一堆无聊的东西面前,你没法把自己彻底想象成另外一个人,没法过上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更没法洗个头就哗啦一下出现在某个美轮美奂的城市,周围全是花天酒地、游手好闲的艺术家。
外面厨房里,水壶发出悲惨的叫声,好像嚷着要求从炉子上拿开似的。劳拉被吓了一跳,想从淋浴头下冲出来,却发现毛巾不在架子上。她听见母亲凯特正在隔壁房间里忙成一团,一边将那只水壶从痛苦中拯救出来,一边像狗儿一样想甩干身体,虽然她一定清楚这丝毫无济于事。
“妈!这儿没毛巾。”劳拉不耐烦地嚷道。这时她在门边的一堆衣服里瞅到一条,赶紧抓在手里,“找到了!找到一条!噢,见鬼!是湿的!”
“先出来才有干毛巾。”凯特在厨房里喊道。
浴室的镜子装在水雾最浓的地方,劳拉只能看到一个模模糊糊的影子。不过这模糊的影子倒正合她的胃口。自己在镜子里的样子总搅得她心烦意乱,最好就这样雾蒙蒙的一片,别太清楚,因为无论她怎样努力想让自己在镜子里看起来与众不同,但结果还是老样子。要是不在镜子前装模作样,她还真想不出自己会成什么样子。不过,劳拉倒是对自己的身体多点信心,这至少让她多那么一丁点乐观吧。
“远远看起来,还凑合吧,”同学尼基曾经告诉她说,“不过走近一看不怎么样。你长得太不显眼儿啦!让你妈带你去做个正点儿的发型,要不在额头前面挑染一缕金发什么的。”
劳拉可不想染什么金发。绝大多数时候。她很乐意这样不显眼,跟妈妈和弟弟杰科一起不显眼地生活在一起。然而,有时候站在镜子前,尼基的话却像句赞美一般再次传来,仿佛在说:如果劳拉自己愿意的话,她是可以变得显眼一点的。
穿过窄窄的客厅,凯特在大点的那间屋子里抱怨起来。
“我不可能在开车的时候弄丢一只鞋,”她说道,“每次换挡就该知道。”
“鞋没了!”杰科报告说。劳拉正裹着湿漉漉的浴巾,奔向卧室。
刚一进门,她猛地停下来。一阵莫名其妙的恐惧蹿上心头,虽然眼前其实什么也没发生。然而劳拉呆在原地,一点也迈不开步子。那恐惧感如此强烈,就像被拨动的琴弦般震颤不停。
“找遍了整个屋子。”凯特那熟悉的腔调再次响起,把劳拉扯回到这个普通而忙乱的早晨。她耸耸肩,暂时放下心头那种难以名状的震颤,胡乱地将校服套在身上——除了内衣,学生都必须穿戴得整齐划一。校服里不包括内衣,总算给女生们留了一点面子。幸好还没有哪所学校不近人情到那个地步。
“一定会发生。”一个声音说。
“发生什么?”问完这个问题,劳拉才发现原来说话的声音其实在她脑袋瓜里,房间里除了自己,连个鬼影子都没有。
这是个警告,劳拉的心一点点往下沉。这种感觉她以前也有过,虽然并不老是如此,但她绝不会忘记这情形。每次警告发生过后,她总觉得自己应该能做点什么,但结果却又总是发现无能为力。因此,这个警告的作用可能只是提醒她,应该做好某种准备。
“鞋还没找到!”杰科站在门口,报告事情的进展。
劳拉拿起梳子,对着房间里那面镜子。这是家里最好的镜子,因为外面的阳光可以从窗户直接照到镜子上。她认真地端详着自己的影子。
“我看起来不那么幼稚吧,”劳拉自言自语着,试着把注意力从警告上挪开,“也许它会觉得无趣,然后自动消失呢。”可惜镜子里的影子却不这样想。镜子里的劳拉看起来更加惴惴不安,更加毛骨悚然。
有时候。细枝末节的改变甚至比面目全非更令人惊恐。要是这时有人问:镜子里的劳拉怎么就不是她本人?可能连她自己也说不清那副模样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明明还是自己的头发、眼睛,眼睛周围长着纤细的乌黑睫毛。这不就是平时她有点沾沾自喜的样子吗?可是,不管怎样,那张脸肯定不是自己的脸。那脸上的表情好像在说:我知道你不知道的秘密。那副神秘兮兮的面孔上,除了恐惧。竟然还莫名其妙地露着些许兴高采烈的表情。那表情千真万确。难以预料的未来想传递的不只是一种警告,而且似乎还在向劳拉发出邀请。
“停下来!”劳拉大声嚷道。每当心里的惧怕到达极限,她往往会有点暴躁不安。她使劲眨了眨眼,甩了甩头。再回过头来看镜子时,一切似乎又恢复正常:一头卷卷的棕发,黑黑的眼瞳,皮肤散发着淡淡的橄榄光泽。跟母亲和弟弟的金发碧眼大不相同,劳拉的基因似乎是在向她的八位曾曾祖父致敬。他们都曾经是勇猛的波利尼西亚武士。
“天哪!”劳拉跑过窄窄的客厅,冲向母亲和杰科共用的卧室。那里粗略一看什么人也没有,因为凯特正趴在地板上,在床底下摸索,搜寻昨晚偷偷躲到下面的鞋子。“妈!”劳拉喊道,“我接到警告了。是真的!”
“你说什么?”凯特的声音从床垫下闷闷地传来,听上去有些不快。
“它又来了。”劳拉说。
“我就知道什么又来了,”凯特说道,但她指的是另一回事,“这是第二回早上碰上麻烦了。谁告诉我一只非常普通——不,非常好,相当贵的——鞋怎么会好端端地跑掉了?答对了发奖。”
“我刚刚照镜子,发现我的影子突然变老了。”劳拉说。
“等到了我这个年龄,你会发现每天早上都会变老点儿。”凯特的声音依然闷闷的,“这里除了灰,什么都没有。”
杰科站在卧室门口,抱着他的鲁吉娃娃,看着她们说话,仿佛在看一场专门为他演出的马戏表演。
“全乱套了,”劳拉嘟囔道,“今天出门一定会有麻烦。我最好是呆在家,哪儿也别去。可以给我写张假条吗?”
“星期四了还请假?”凯特终于从床底下爬起来,拍掉手里的灰尘,“你想哪儿去了,劳拉!星期四是我最需要你帮忙的日子啊。今天我得加夜班。不然谁去接杰科回家,做晚饭,读故事哄他睡觉?星期四不许请假,就这么定了。”
“又不是我定的日子,”劳拉说,可她的声音却已经偃旗息鼓,“是警告选了今天。”
“谁也不能选星期四。”凯特固执地说,似乎只要将胡思乱想一股脑儿拒之门外,就能掌握命运一样。“只要加倍小心就行了!过马路看两边!别跟老师对着干!”
“妈!不是你说的那样!”劳拉反驳道,“有东西在警告我们:一定会发生什么严重的事情。只是你不知道究竟是什么而已!”
“等会儿再告诉我。”凯特回答道,但劳拉明白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那种情形似乎超出了语言可以描述的范围。别人必须相信她说的一切,但让人相信这些乱七八糟的话比登天还难,尤其是在这个慌慌张张的早晨。生活在朝着三个不同的方向前进,而其中只有一个方向归她管。
这时。凯特突然灵光一闪记起什么来。咚咚咚咚冲进大房间,在壁炉架上找到了自己的另外一只鞋。昨晚在空荡荡的壁炉边,欣赏杰科画的一幅画——画的是快乐的一家人,这是杰科目前唯一会画的画,凯特不知不觉中将那只鞋子放在那里了。那幅画上是他们一家三口:劳拉、杰科和凯特。模样有点可笑,但总算有胳膊有腿。颤巍巍的小短腿配上硕大无朋的脑袋瓜。脸上的笑容无比灿烂,嘴巴几乎都要笑出脸蛋儿落到纸上了。这笑容的效果不错,凯特很快放松下来,步子也迈得安稳了不少。鞋子总算物归原主,她也立即打算尽弃前嫌,饶恕它先前失踪的小把戏了。
但对劳拉来说,要跟眼前这一团乱糟糟的情形握手言和却不那么简单。几分钟前还轻松惬意的一天现在却变得异常凝重起来。仲夏的天空似乎想要将整个身体压在劳拉家的房顶上,冲着她喘着热乎乎的粗气。
“你的篮子在哪儿,杰科?”凯特问道。杰科飞快跑去拿出他的篮子。里面装着洗干净的毛线衫、儿童内衣、过图书馆家家用的书、虎宝宝书,还有“罗斯巴德”——一只笑嘻嘻的粉红色玩具鳄鱼。他的鲁吉娃娃则小心翼翼地放在这一篮子宝贝似的财产的最上面。
“好啦!”凯特说,“我们在路上边走边说好吗?我希望你感觉好点儿了,劳丽(劳拉的昵称),今天早上一定又很难发动我们那车子。”



